|
《光明日报》记者探访了一座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村庄:

凌晨3点,原隆村的村民就在茫茫夜色中排队,等待接驳的车辆,然后坐一小时的车,前往私人资本承包的葡萄园劳动。干到中午12点,一天八个小时劳动,挣100元;每拉一个“劳动力”,劳务中介可以得到20元……



光明日报的博文写道:“在这条奔向乡村振兴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适合自己的位置,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开拓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记者看到的是满满的“幸福”,笔者看到的却是生存的不易。
“凌晨三点起床”、就近当“农业工人”,这比起二十年前的贫困村的确强多了。但笔者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在当地农民自己土地上流转出去建立的葡萄园是农民自己办的,他们的收益恐怕就不仅仅是“干一天100元”了吧?而熟悉农业劳动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干一天100元”的工作并不稳定,农业资本在支付了这部分低廉报酬之外,并不支付农民的社保,乃至“负担”各种社会福利。此外,如果每个村村民都有自己合办的葡萄园或者蔬菜基地、粮食基地,也许就不用成为流动的临时劳动力跑这么远的路了吧?

看到车上满载的农民务工者,光明日报的微博下面,也有网友表示了担忧: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
今年9月4日凌晨4点,黑龙江省勃利县境内一重型半挂车与拖拉机相撞,致15死1伤;
仅仅过了一天,惨剧再一次发生,9月5日,安徽省太湖县境内一皮卡车坠入山沟,致12人遇难。

两起交通事故的背后有着共同的背景:发生事故的车辆都有超载等违规行为;遇难者都为农业务工人员……
而此类的交通事故,其实是折射出了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以及资本下乡的规模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个体农民已经彻底转换了身份,成为“职业”的农业雇佣劳动工人。
当然,因为现阶段的土地流转暂时限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农民名义上还具有对土地承包的支配权,这样的农业雇佣劳动者还不能算着严格意义的农业无产者。不过,随着各地为了“增强流转的稳定性”,不断延长流转周期和规模,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实际上是在不断虚化。
因为农业生产本身的时节性以及农产品周期性的市场震荡,这样的“职业”并不稳定,往往呈现的是短期、临时性用工,工种比较纷杂但对技能要求普遍不高,例如剪枝、除草、施肥、打药、采摘、搬运及包装等。因此也就造成劳动关系很难被法律固定,劳动强度大、待遇却普遍较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从业者一般为当地的中老年农民。
笔者曾经在成都周边的几个地级市下面的农村地区做过调研,类似的葡萄基地、柚子基地、猕猴桃基地或者蔬菜基地大量地存在着,实际的工资水平甚至还比不上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中给出的数字,一般每天的工资在60~80元,碰到农忙时节工资能到100,但每日工作时间也要在10小时以上。
而现在的葡萄都是采用大棚种植,到了喷洒农药的季节,被雇佣的农民往往只是戴上一个简单的口罩就要进到大棚作业。笔者站在大棚外面都因为农药散发的味道感觉晕眩,农民在大棚作业要忍受怎样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出现之前,个体农户种植蔬菜或者经济作物的也不少,但是水果蔬菜收货之后的储存周期一般都比较短,农民要想尽快出售掉,就只能卖给仅存收购的经销商人,个体农民基本不具备议价权;而市场的追涨杀跌也使农民不断面临着“多收三五斗”的困境,经常亏得血本无归。
农业资本下乡以后的规模化经营,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问题。不可否认,资本下乡比起原有的小农经济模式,的确带来了局部的经济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资本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已提供过另外一种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将西海固地区的农业雇佣劳动者描述为“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开拓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将这样的模式描述成乡村振兴和农民脱贫的典型,但是,这样的描述遮蔽了资本下乡和雇佣劳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2019年第3期《开放时代》杂志刊登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陈航英教授针对西海固地区的黄高县资本下乡状况的深度调查报告《干涸的机井:资本下乡与水资源攫取——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蔬菜产业为例》。
这篇调查文章指出,黄高县的蔬菜种植可追溯到1996年。2002年,“中国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援建黄高县三百栋节能日光温室,当地政府希望借助发展蔬菜产业促进当地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完成当地脱贫攻坚。市场滞销时,农户亏损严重;市场紧俏时,个体农户又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加之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不断增加,农户逐渐退出蔬菜种植。
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各类资本进入项目区流转土地展开规模经营。然而,在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发展蔬菜规模经营过程中已经出现水资源攫取现象。黄高县整体上属于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当地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满足农户生活和生产的用水需求。伴随蔬菜项目区的建设,“项目井”开始出现,取水量和取水速度大大超过之前的个体农户取水,地下水超采严重,原住农户的私人井就要断水。而为了保护资本下乡积极性,基层政府开始通过一些手段排斥本地农户的用水权益。
与之同时,这也是一种涸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这种方式取得的发展成果又有多少能够真正回馈给当地民众?
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当地农民,除了能够获得一点点低廉的劳动报酬,未来的生存前景却是堪忧的。而资本本身是可流动的,下乡资本并不需要顾及这些问题,他们大不了再去开垦下一块“处女地”……
作为资本下乡的替代模式,西海固地区同样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辉煌时期,只是这在后来被描述为“贫困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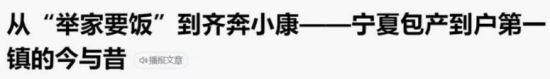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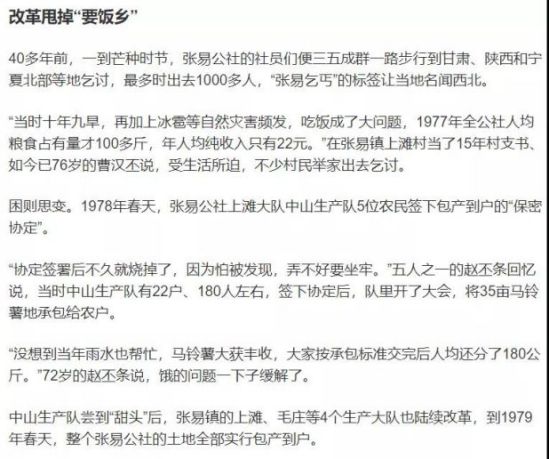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张易公社的上滩大队,在1964年却也曾被当作先进典型报道过:


历史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恐怕要留给后人书写。但大寨的道路乃至目前还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南街、华西,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恐怕才是农民真正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